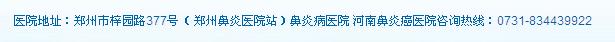瓜蒌红花甘草汤,见于《医旨绪余》。现在,经临床使用观察,瓜蒌红花甘草汤可与其它方剂化裁合用,可用来治疗带状疱疹,收到良好的效果。
案例1:
《医旨绪余》记载了一个案例:
我弟弟在六月份进城,途中受热而且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降低),况且他平时性格多暴躁,于是忽然出现左边胁肋疼痛,皮肤上发红一片像碗口般大,而且发了三五点水泡,脉象紧张像琴弦一般,且脉来较快,一呼一吸间脉跳7下,夜间发作的比白天更厉害。医生认为这是肝经的郁火(火热郁结,不能散开),于是开了些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的药。喝了一次药之后,当天晚上疼痛的更厉害而且局部更加热了。第二天早上一看,皮肤上发红的范围变成盘子那么大了,而且水泡疮又增加到三十多颗。
然后医生又让用白矾研粉末,用井水调敷,仍用前面的处方加入青黛、龙胆草再服。这天晚上我弟弟痛苦不己,惨叫之声响彻四邻,胁肋中痛的就像用刀割用钩摘一样。笫二天再看,皮肤上发红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半边身子了,水泡又增加到了百来个。我心中很难过,于是把他接回来找我的老师黄古潭先生。先生看过脉案药方,冷冷一笑道:切脉认证是没错了,但制药定方还差得远呢。要知道用药像用兵一样,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现在病情像叠着鸡蛋一样危急,如何还能用这些寻常的泻肝的药来治疗呢?这就像让羊去打老虎一样。况且苦寒的药会化燥,因此喝药之后病情更加重了。皮肤上发水泡,是因为肝郁久了,不能发出来,所以侮其所不胜(五行生克中,金克木为常态,被木克则称为侮。肺为金,主皮肤,肝为木。然而肝火反伤皮肤,所以是木侮金。),所以皮肤破溃,火势急迫,甚至于像自焚一般死去,及其可怕。
然后黄先生拟定了一个方子,用重一、二两的大瓜蒌一个,连皮捣烂,加甘草二钱,红花五分,戌时(19:00-21:00)进药,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到子丑(子时:23:00-01:00,丑时:01:00-03:00)时分才醒,问他说已经不痛了。于是要吃东西,我想火邪未退干净,不敢给吃的,怕食物助火。于是又把药渣煎了给他喝下去,又睡到第二天早上,中间解过一次稀便,到早上7-9点起来一看,皮肤的红肿已经消失了,水泡疮也尽数消失了,后面也没吃其他药就好了。
孙一奎感叹道:接连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痛到呻吟不停的重病,一剂而愈,真可说的上是神了。
然后孙一奎在后面写了段按语来总结,说,瓜蒌这个药,性味甘寒,柔而润滑,滑则于郁不冲突,润则不伤津液,甘则能缓和情势,寒则能清火热。《难经》说“损其肝者,缓其中”,考据本草,瓜蒌能治疗胁肋疼痛,大约是它能够缓急润燥而且流通,所以痛自然而然止住了。
案例2:
邹孟城说:余得此方,喜不自禁,盖“医家之病,病道少”。为医者能多一治病法门,则病家少一份痛苦。……未几,疱疹流行,余于数日内接治五六人,无论证之轻重,皆以上方加板兰根15克予服,惟全瓜蒌不用如许之多,改为重者30克,轻者15克,中者21-24克,其收效之速,“真可谓之神矣”。轻者二三日,重者四五日,率皆痊可。本方得效之迟速,与瓜蒌用量极有关系,故凡体质壮实者,瓜蒌用量宜适当加重,药后若轻泻一二次,则见效尤速。……关于甘草,余有时仅用3克,同样有效,而红花每以1.5克为率,并不多用,而屡收捷效。
案例3:
黄某某,男性,47岁。年8月24日初诊。起病5天,右臀至大腿外侧出现大片带状成簇水疱,疼痛剧烈。外院以西药抗病毒、止痛等治疗,无明显改善。口苦不干,二便可,舌偏暗,苔中白,脉沉细。有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塞、糖尿史。予芍药甘草汤合瓜红草方加味:瓜蒌60g,红花10g,甘草20g,白芍60g,全虫7g,蜈蚣2条,苍术15g,茯苓15g,桔梗30g,2剂。外用紫金锭醋调外敷,甘马醋剂(炙甘草3g,制马钱子3g,白醋50ml浸泡,2小时后蘸液外搽痛处)外搽。两剂后,疼痛减轻,水疱渐干涸。前方加牛膝30g,全虫加至9g。再服2剂,疼痛若失,守方3剂而愈。附:外用药
外科中的二味拔毒散,方用:白矾,雄黄各等份,研为细末,凉开水调涂,一日数次。(注:干了则再涂)《金鉴》称:此散治风湿诸疮,红肿痛痒,疥痱等疾甚效,用鹅翎蘸扫患处,痛痒自止,红肿即消。但并未言及治带状疱疹,即缠腰火丹。
经临床运用得知,在刚起的阶段就快用此药,基本上可以不必配用其他药物。但对治疗不及时,已经形成较大面积疱疹和溃疡者,应结合其他疗法,比如西医的常规疗法,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此方可以称得上是药简效宏的一个好处方。使用时用香油调涂也可以,但我的经验不如用凉开水,因为用水涂上干的快,有利于快点结疤,且不宜弄脏衣服。
至于用香油还是用凉开水来调药,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刚开始,皮肤没有化脓,用凉开水调药,结疤快,好的也快。但如果皮肤已经化脓,用凉开水调药往往在皮肤上结成一层厚疤,就会形成疤下化脓更加厉害,所以在头几天应该用香油调药,待炎证消退后,脓液渐清,再用凉开水调药,效果才好。治疗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其它情况,我也不能一一预料,相信大家会随证处理的,就不多说了。
附孙一奎原文:
余弟于六月赴邑,途行受热,且过劳,性多躁暴,忽左胁痛,皮肤上一片红如碗大,发水泡疮三五点,脉七至而弦,夜重于昼。医作肝经郁火治之,以黄连、青皮、香附、川芎、柴胡之类,进一服,其夜痛极,且增热。次早看之,其皮肤上红大如盘,水泡疮又加至三十余粒。医教以白矾研未,井水调敷,仍于前药加青黛、龙胆草进之。其夜痛苦不已,叫号之声,彻于四邻,胁中痛如钩摘之状。次早观之,其红已及半身矣,水泡疮又增至百数。予心甚不怿,乃载归以询先师黄古潭先生,先生观脉案药方,哂曰∶切脉认病则审矣,制药订方则未也。夫用药如用兵,知已知彼,百战百胜,今病势有烧眉之急,迭卵之危,岂可执寻常泻肝之剂正治耶?是谓驱羊搏虎矣!且苦寒之药,愈资其燥,以故病转增剧。水泡疮发于外者,肝郁既久,不得发越,乃侮其所不胜,故皮腠为之溃也,至于自焚则死矣,可惧之甚!为订一方,以大栝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戌时进药,少顷就得睡,至子丑时方醒,问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恐邪火未尽退也。急煎药渣与之,又睡至天明时,微利一度,复睡至辰时。起视皮肤之红,皆已冰释,而水泡疮亦尽敛矣,后亦不服他药。夫病重三日,饮食不进,呻吟不辍口,一剂而愈,真可谓之神矣。
夫栝蒌味甘寒,《经》云∶“泄其肝者,缓其中。”且其为物,柔而滑润,于郁不逆,甘缓润下,又如油之洗物,未尝不洁。考之本草,栝蒌能治插胁之痛,盖为其缓中润燥,以致于流通,故痛自然止也。
大瓜蒌一枚,重一二两者,连皮捣烂,加粉草二钱,红花五分,戌时进药,少顷就得睡,至子丑时方醒,问之,已不痛矣。乃索食。予禁止之,思邪火未尽退也。急煎药渣与之。又睡至天明时,微利一度,复睡至辰时,起视,皮肤之红皆已冰释,而水泡疮也尽敛矣,后也不服他药。
注:仅供学习参考,切莫随意尝试。
长按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