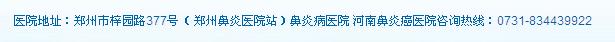林毅夫:我国有条件保持7.5左右中高速增长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探索世界经济全面复兴之路 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危机后,世界经济并没有实现多数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复苏。继《新结构经济学》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框架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另外1本专著《从西潮到东风》中,又系统地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作出了深入分析,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复苏提出了系统性的建议,并就如何避免一样的危机在未来再次产生提倡了他的独到主张。 世界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复苏之路何在?在普遍唱衰中国经济的背景下,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还有20年左右高速增长潜力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未来改革发展之路在哪里?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近日专访了林毅夫。 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为结构改革赢得空间 第一财经:您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其实不代表潜伏增速的趋势性着落,而主要由全球性经济周期衰退所导致。您这几年一直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对发达国家走出衰退有何系统性建议? 林毅夫:发达国家出现危机后,需要实行下落工资和福利、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减少政府赤字和金融机构去杠杆等结构改革,经济才能恢复动力和正常增长。 但结构改革是收缩性的,最少在短期内会减少投资和消费,下落经济增速,提高失业率。而危机国家本身失业率已很高,急速推行这些结构改革难免会触发社会和政治动乱。国际上类似例子很多。危机国家向国际社会申请支援时许诺的结构改革,常常不会付诸实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救助危机国家时有三个政策。前两个是实行结构改革,和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和就业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这两个措施见效都需要一段时间,因此通常会辅助以第三个政策,即提供短期贷款和支援。 目前这个策略基本不可用。堕入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没有自己的独立货币,没法实行贬值带动出口、增加就业,为结构改革创造空间。虽然欧洲可通过欧元整体贬值方式到达全面刺激出口的效果,但却受制于美日,由于,欧元区国家出口的产品和美日相同,欧元区增加出口、创造就业的代价是美日减少出口、增加失业,但是,美国、日本也一样由于惧怕失业增加而还没有推行结构性改革,因此,欧元区或美日想以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都会遭到其他国家以竞争性贬值来对冲,而没法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所需的空间。 由于这次危机是在发达国家同时产生,其GDP总和占全球很大份额,因此,目前来看发达国家很难进行结构性改革而真正走出危机。表面上的一些复苏是很脆弱的。综合GDP和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指标的情况看,大的反弹并没有出现。 因此,我认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必须想出一个与货币贬值有一样效果的办法,以便为结构改革创造空间。2008年时,很多人认为危机很快过去,但6年以后的今天仍未见起色,所以我在2008年危机刚产生时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为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和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消除瓶颈的共赢建议,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鸣。 :倘若上述刺激措施能使发达国家走出衰退、由发达国家带动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尚未能重新确立,那么,对过去一段时期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下阶段新的发展动力何在?这正是本届论坛的主题。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个议题有什么主张? 林毅夫:外需相对疲软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固然要转向内需。内需包括投资与消费。前段时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转向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但重新结构经济学框架动身,我不主张这类政策。消费固然很重要,但消费增长的条件是收入不断增长,否则就得举债。发达国家危机很多正是过度消费造成的。 收入持续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率提高又依赖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交易费用不断着落。其中,交易费用着落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因此,增加消费是逻辑链条的终端结果,而这个链条的出发点则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完善上的高效投资。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这些有效投资的空间非常大。另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财政状态较好,民间储蓄高,外汇储备多。利用好这些条件的话,我国保持在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轨道是没有问题的。 深挖后发优势 推动中国未来20年高速发展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时间的奇迹式增长取得了普遍关注,但近期唱衰中国的声音再次显现,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林毅夫: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大部分观点认为是中国体制机制的内在缘由造成的,而改革体制机制又很难,因此他们认为增长不可延续。唱衰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崩溃论一直都有,主要是由于中国一直未按西方的主流理论去进行改革。我们确切有很多问题。但唱衰论调没有看清增长放缓的缘由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 我近期参加的很多国际会议上,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放缓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但为何在我们经济放缓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和我们一样发展程度的国家如印度和巴西,和东亚那些表现很好的新兴高收入经济体,增速也在放缓,而且放缓程度比我们还大?因此这类同步放缓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 我们在听国外人士发表看法时,要保持苏醒的认识。例如,美国QE3退出造成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大量资金外流,给它们的宏观经济管理造成很大困难,印度的中央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拉祜·拉贾要求美国的货币政白癜风怎样治最好策不能只照顾美国自己的利益,而应当顾及全球的影响,但美联储最近发表文章提出了"脆弱性的六个指标",认为QE3退出时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经济脆弱性造成的。印度、巴西、印尼等国这6个指标都很差,但中国的却很好。 而这6个指标中外贸盈余多、外汇积累大、储蓄率高在过去则都曾被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延续的,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缘由,但在这次的脆弱性评价中却变成了中国被称赞为经济稳定强健性高的缘由。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所以,不能简单地根据发达国家或是国际机构的说法舞蹈,发达国家品评我们时,我们必须苏醒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结果如何。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减缓才能推动改革。我认为这类思路其实不完全对,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再加上原有体制机制的一些问题,政府极可能就变成"救火队"。改革必须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从容展开,如果疲于"救火",根本没法做长远规划和改革。因此保持一定增速是必要的,特别在下滑由外部条件造成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而且,我们现在有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条件,这点和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相同。 :那您对未来中国发展潜力有何具体看法? 林毅夫:重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我相信中国从2008年起还有20年高速增长的潜力。潜力就在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所决定的巨大后发优势。利用好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很多,相应的投入和风险也都小于发达国家。 目前有两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奇迹不过就是20年,中国已高速增长35年,放慢是一定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均GDP到达11000美元的时候,增长速度就会放缓。我们将很快到达这个水平,所以必然会放缓。 但这些说法其实不准确。衡量一个国家后发优势的标准是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由于人均收入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产业附加值水平。 依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这些经济体分别在那些年份以后,利用后发优势实现20年左右8~9的增长。所以,中国从2008年开始也应当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潜力。 日本人均GDP超过11000美元时,人均收入已超过美国水平的65了,后发优势已比较小。依照我的测算,我国人均GDP在2015年前后会到达11000美元的水平,但届时我们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30,潜力还很大。 所以我认为,历史经验不能机械地照搬,必须理解它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改革新路径:由双轨制走向单轨制 :"双轨制"在中国以往发展进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也被认为是目前发展的制约。回顾中国经济以往35年的发展历史,您对这1转型路径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转型中国家一定有制度扭曲。比较标准模型来看,这些扭曲一定带来效率损失,这个必须承认。但改革必须从实际动身,条件成熟时才可以改,而且必须改。我向来反对简单地拿发达国家经验、体制和盛行的理论作为标杆,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情形。 20年前我和蔡昉、李周一起合作著作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当时世界上主流看法是华盛顿共鸣,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前者向后者过渡应采取大爆炸或休克疗法。最糟的是双轨制,如果不是一次性消除原来的制度扭曲,那么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还糟。 在那本书中,我们认为转型国家要同时实现稳定和快速地发展,必须采取渐进双轨的方式。我们与主流看法最大的不同是,指出了原来的制度扭曲、价格扭曲等,是内生的,内生决定于上世纪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不是如休克疗法者所认为的外生的政府干预。 当时我们提出"自生能力"新概念。含义是:有着正常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如果不依托政府保护和补贴能够存续,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就没有自生能力。 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重工业企业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国家必须给予保护和补贴比如说垄断和低投入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和资源价格等,才能经营下去。这固然会影响效率,但在转型过程中将这些补贴都立即取消的话,会造成大量破产和失业。更何况那些企业即使到现在也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 当时围绕国企改革问题,我与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过辩论。当时的主流看法是,由于这些企业是国企,所以才给予保护补贴。但我认为保护补贴的缘由是,它们没有自生能力,却由于就业或国防安全的推敲,而必须存在。倘若这类背景下将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私有化,必须给他们更多补贴。由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国有的时候,员工都是国家雇员,顶多只能多吃,多拿就是犯法,这就对补贴有一定限制。而私有化以后,多拿是合法的,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因此,私有化以后为了让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存续下去,支付的补贴会更多,腐败会更普遍。我的观点已为后来苏联东欧私有化以后的情况所证实。而实行双轨制的中国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如果说以往我国走双轨制转型路径、补贴国有企业有合理性的话,今天是否是应当对此加以改革? 林毅夫:改革应当与时俱进。双轨制在以往具有合理性,其实不意味着不需要改革。去年我国人均GDP已到达6800美元,资本已相对丰富,除极少数与国防等有关的企业,绝大多数重工业其实已符合比较优势了。这说明这个产业中的企业有自生能力,不需要保护补贴,只要改进经营就能获利。这样情况下,补贴就变成锦上添花,就需要改革。 今天实行相干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现在,绝大部分产业已符合比较优势,具有市场竞争力。所以我非常赞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尚存的市场扭曲取消掉,构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 :基于您对发展理论演变的深入认识,和您的全球视野的视察,您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国政策设计最应当注意避免哪些偏向? 林毅夫:从《中国的奇迹》那本书开始,我们就说中国双轨渐进改革的好处是稳定快速的发展,代价是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大等。 中国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断扩大的差距造成的人们心理失衡越发严重。而且这类差距还跟腐败联系在一起,就更引发了对这个体制合法性的质疑。要稳定才能发展。所以,这个问题现阶段改革必须加以解决,但必须对症下药。我认为这个"症"目前来说就是双轨制下对一些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对市场的垄断。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现在深化改革的方向就是改正那些已不合适的制度。例如腐败的根源在于有租金,有租金就有寻租。如果将扭曲取消掉,就不存在租金,寻租自然就会减少。这是"釜底抽薪"。 领头龙带给低收入国家的黄金机遇期 :为逾越中等收入骗局,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延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给那些目前仍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的8亿人口,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带来哪些机遇?如何让这些国家也融入到全球发展进程中来? 林毅夫:2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普遍不成功。缘由在于他们基本上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做参照,但历史基础和现实状态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过去半个多世纪有几个发展中经济体已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虽然很多政策不能机械照搬,但成功背后的道理是可以参考的。 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对别的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黄金机遇。医治白癜风要多久这在历史上也有经验,如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产业转移,就给当时的亚洲4小龙提供了战略机遇,80年代亚洲4小龙的产业转移也一样给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机遇。 过去讲的是雁行模式,现在我讲领头龙模式。中国大陆现在制造业雇佣1.5亿人。中国制造业升级所释放出来的机会,可以说是二战以后第三次转移,对其他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捉住这个机遇,就必须构成一个"有为的政府",顺手推舟地克服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一定遇到的外部性问题,并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充分发挥后发优势。